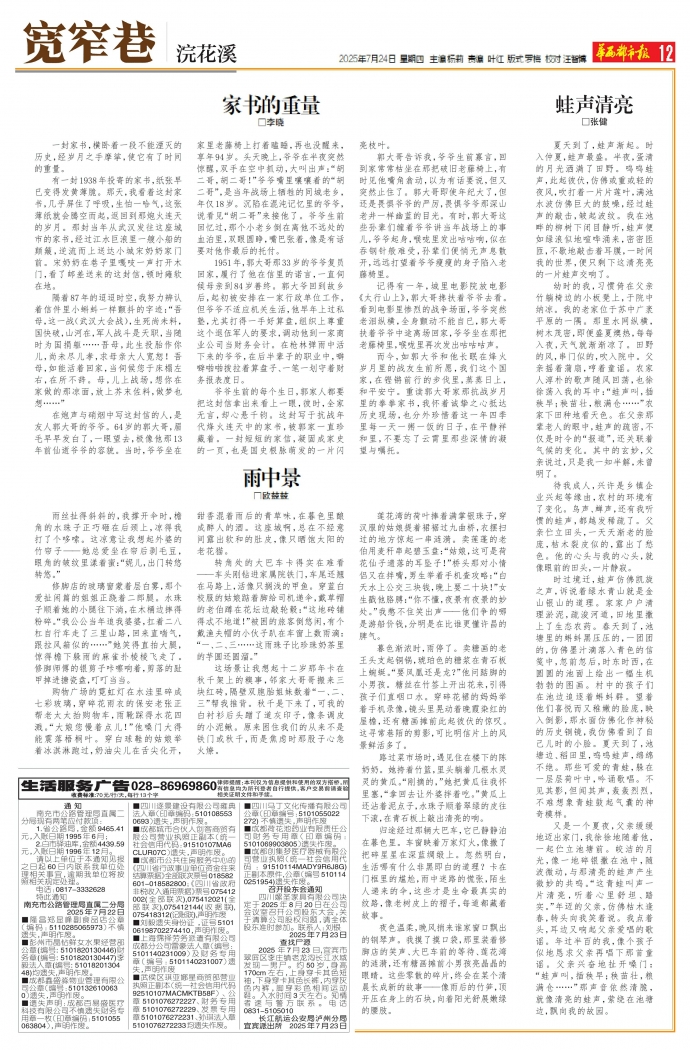蛙声清亮
□张健
夏天到了,蛙声渐起。时入仲夏,蛙声最盛。半夜,蛋清的月光洒满了田野。鸣鸣蛙声,此起彼伏,仿佛或重或轻的夜风,吹打着一片片莲叶,满池水波仿佛巨大的鼓噪,经过蛙声的敲击,皱起波纹。我在池畔的柳树下闭目静听,蛙声便如绿浪似地喧哗涌来,密密匝匝,不歇地敲击着耳膜,一时间我的世界,便只剩下这清亮亮的一片蛙声交响了。
幼时的我,习惯倚在父亲竹躺椅边的小板凳上,于院中纳凉。我的老家位于苏中广袤平原的一隅。那里水网纵横,树木茂密,即便盛夏燠热,每每入夜,天气就渐渐凉了。田野的风,串门似的,吹入院中。父亲摇着蒲扇,哼着童谣。农家人淳朴的歌声随风回荡,也徐徐荡入我的耳中:“蛙声叫,插秧早;秧苗壮,粮满仓……”农家下田种地看天色。在父亲那辈老人的眼中,蛙声的疏密,不仅是时令的“报道”,还关联着气候的变化。其中的玄妙,父亲说过,只是我一知半解,未曾明了。
待我成人,兴许是乡镇企业兴起等缘由,农村的环境有了变化。鸟声、蝉声,还有我听惯的蛙声,都越发稀疏了。父亲伫立田头,一天天渐老的脸庞,枯木裂皮似的,露出了愁色。他的心头与我的心头,就像眼前的田头,一片静寂。
时过境迁,蛙声仿佛凯旋之声,诉说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家家户户清理淤泥,疏浚河道,田地里撒上了生态农药。春天到了,池塘里的蝌蚪黑压压的,一团团的,仿佛墨汁滴落入青色的信笺中,忽前忽后,时东时西,在圆圆的池面上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图画。村中的孩子们在池边追逐着蝌蚪群。望着他们喜悦而又稚嫩的脸庞,映入倒影,那水面仿佛化作神秘的历史铜镜,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儿时的小脸。夏天到了,池塘边、稻田里,鸣鸣蛙声,绵绵不绝。那些可爱的青蛙,躲在一层层荷叶中,吟诵歌唱。不见其影,但闻其声,轰轰烈烈,不难想象青蛙鼓起气囊的神奇模样。
又是一个夏夜,父亲缓缓地迈出家门,我徐徐地随着他,一起伫立池塘前。皎洁的月光,像一地碎银撒在池中,随波微动,与那清亮的蛙声产生微妙的共鸣。“这青蛙叫声一片清亮,听着心里舒坦、踏实。”年迈的父亲,仿佛枯木逢春,转头向我笑着说。我点着头,耳边又响起父亲爱唱的歌谣。年过半百的我,像个孩子似地恳求父亲再唱下那首童谣。父亲兴奋地扯开嗓门:“蛙声叫,插秧早;秧苗壮,粮满仓……”那声音依然清脆,就像清亮的蛙声,萦绕在池塘边,飘向我的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