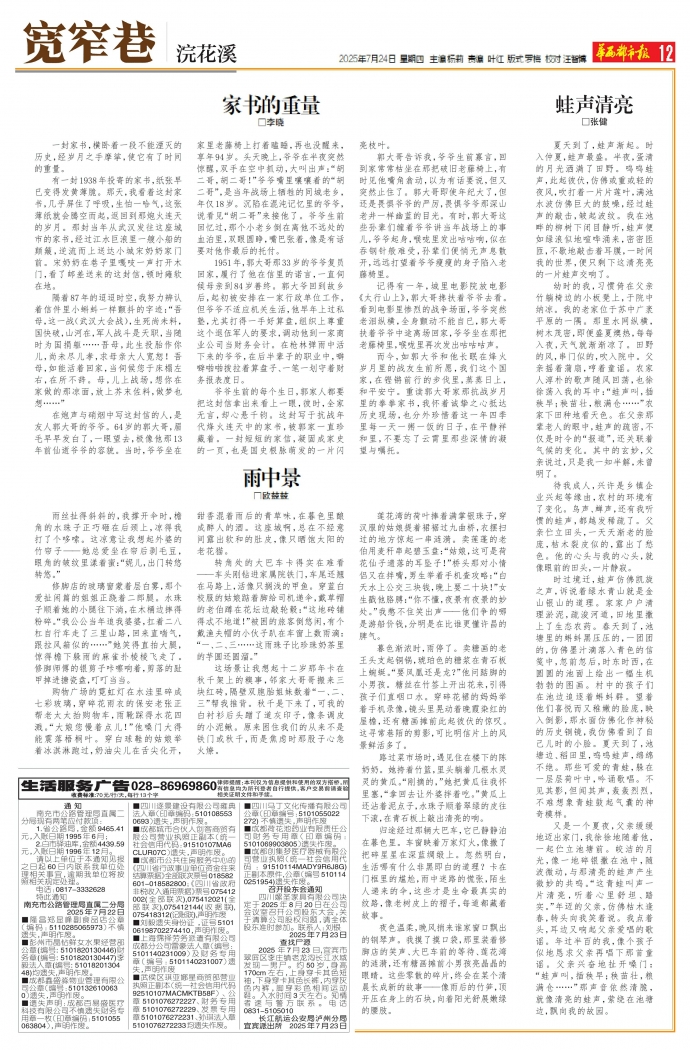家书的重量
□李晓
一封家书,横卧着一段不能湮灭的历史,经岁月之手摩挲,使它有了时间的重量。
有一封1938年投寄的家书,纸张早已变得发黄薄脆。那天,我看着这封家书,几乎屏住了呼吸,生怕一哈气,这张薄纸就会腾空而起,返回到那炮火连天的岁月。那封当年从武汉发往这座城市的家书,经过江水巨浪里一艘小船的颠簸,逆流而上送达小城宋奶奶家门前。宋奶奶在巷子里嘎吱一声打开木门,看了邮差送来的这封信,顿时瘫软在地。
隔着87年的迢迢时空,我努力辨认着信件里小蝌蚪一样颤抖的字迹:“吾母,这一战(武汉大会战),生死尚未料,国快破,山河在,军人战斗是天职,当随时为国捐躯……吾母,此生投胎作你儿,尚未尽儿孝,求母亲大人宽恕!吾母,如能活着回家,当伺候您于床榻左右,在所不辞。母,儿上战场,想你在家做的那凉面,放上芥末佐料,做梦也想……”
在炮声与硝烟中写这封信的人,是友人郭大哥的爷爷。64岁的郭大哥,眉毛早早发白了,一眼望去,极像他那13年前仙逝爷爷的容貌。当时,爷爷坐在家里老藤椅上打着瞌睡,再也没醒来,享年94岁。头天晚上,爷爷在半夜突然惊醒,双手在空中抓动,大叫出声:“胡二哥,胡二哥!”爷爷嘴里嚷嚷着的“胡二哥”,是当年战场上牺牲的同城老乡,年仅18岁。沉陷在混沌记忆里的爷爷,说看见“胡二哥”来接他了。爷爷生前回忆过,那个小老乡倒在离他不远处的血泊里,双眼圆睁,嘴巴张着,像是有话要对他作最后的托付。
1951年,郭大哥那33岁的爷爷复员回家,履行了他在信里的诺言,一直伺候母亲到84岁善终。郭大爷回到故乡后,起初被安排在一家行政单位工作,但爷爷不适应机关生活,他早年上过私塾,尤其打得一手好算盘,组织上尊重这个退伍军人的要求,调动他到一家商业公司当财务会计。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爷爷,在后半辈子的职业中,噼噼啪啪拨拉着算盘子、一笔一划守着财务报表度日。
爷爷生前的每个生日,郭家人都要把这封信拿出来看上一眼,彼时,全家无言,却心悬千钧。这封写于抗战年代烽火连天中的家书,被郭家一直珍藏着。一封短短的家信,凝固成家史的一页,也是国史根脉萌发的一片闪亮枝叶。
郭大哥告诉我,爷爷生前寡言,回到家常常枯坐在那把破旧老藤椅上,有时见他嘴角翕动,以为有话要说,但又突然止住了。郭大哥即使年纪大了,但还是畏惧爷爷的严厉,畏惧爷爷那深山老井一样幽蓝的目光。有时,郭大哥这些孙辈们缠着爷爷讲当年战场上的事儿,爷爷起身,喉咙里发出咕咕响,似在吞钢针般难受,孙辈们便悄无声息散开,远远打望着爷爷瘦瘦的身子陷入老藤椅里。
记得有一年,城里电影院放电影《太行山上》,郭大哥搀扶着爷爷去看。看到电影里惨烈的战争场面,爷爷突然老泪纵横,全身颤动不能自已,郭大哥扶着爷爷中途离场回家,爷爷坐在那把老藤椅里,喉咙里再次发出咕咕咕声。
而今,如郭大爷和他长眠在烽火岁月里的战友生前所愿,我们这个国家,在铿锵前行的步伐里,蒸蒸日上,和平安宁。重读郭大哥家那抗战岁月里的拳拳家书,我怀着诚挚之心抵达历史现场,也分外珍惜着这一年四季里每一天一粥一饭的日子,在平静祥和里,不要忘了云霄里那些深情的凝望与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