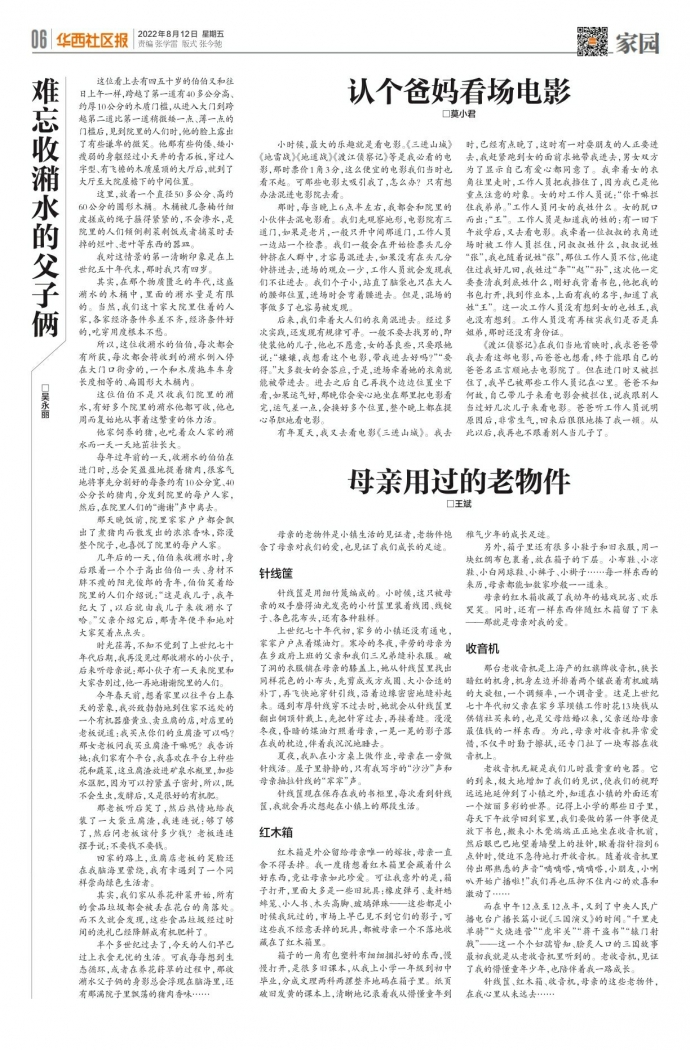母亲用过的老物件
□王斌
母亲的老物件是小镇生活的见证者,老物件饱含了母亲对我们的爱,也见证了我们成长的足迹。
针线筐
针线筐是用细竹篾编成的。小时候,这只被母亲的双手磨得油光发亮的小竹筐里装着线团、线锭子、各色花布头,还有各种鞋样。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家乡的小镇还没有通电,家家户户点着煤油灯。寒冷的冬夜,辛劳的母亲为在乡政府上班的父亲和我们三兄弟缝补衣服。破了洞的衣服铺在母亲的膝盖上,她从针线筐里找出同样花色的小布头,先剪成或方或圆、大小合适的补丁,再飞快地穿针引线,沿着边缘密密地缝补起来。遇到布厚针线穿不过去时,她就会从针线筐里翻出铜顶针戴上,先把针穿过去,再接着缝。漫漫冬夜,昏暗的煤油灯照着母亲,一晃一晃的影子落在我的枕边,伴着我沉沉地睡去。
夏夜,我趴在小方桌上做作业,母亲在一旁做针线活。屋子里静静的,只有我写字的“沙沙”声和母亲抽拉针线的“窣窣”声。
针线筐现在保存在我的书柜里,每次看到针线筐,我就会再次想起在小镇上的那段生活。
红木箱
红木箱是外公留给母亲唯一的嫁妆,母亲一直舍不得丢掉。我一度猜想着红木箱里会藏着什么好东西,竟让母亲如此珍爱。可让我意外的是,箱子打开,里面大多是一些旧玩具:橡皮弹弓、麦杆蟋蟀笼、小人书、木头高脚、玻璃弹珠——这些都是小时候我玩过的,市场上早已见不到它们的影子,可这些我不经意丟掉的玩具,都被母亲一个不落地收藏在了红木箱里。
箱子的一角有包塑料布细细捆扎好的东西,慢慢打开,是很多旧课本,从我上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分成文理两科两摞整齐地码在箱子里。纸页破旧发黄的课本上,清晰地记录着我从懵懂童年到稚气少年的成长足迹。
另外,箱子里还有很多小鞋子和旧衣服,用一块红绸布包裹着,放在箱子的下层。小布鞋、小凉鞋、小白网球鞋、小裤子、小褂子……每一样东西的来历,母亲都能如数家珍般一一道来。
母亲的红木箱收藏了我幼年的嬉戏玩劣、欢乐哭笑。同时,还有一样东西伴随红木箱留了下来——那就是母亲对我的爱。
收音机
那台老收音机是上海产的红旗牌收音机,狭长暗红的机身,机身左边并排着两个镶嵌着有机玻璃的大旋钮,一个调频率,一个调音量。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父亲在家乡草坝镇工作时花13块钱从供销社买来的,也是父母结婚以来,父亲送给母亲最值钱的一样东西。为此,母亲对收音机异常爱惜,不仅平时勤于擦拭,还专门扯了一块布搭在收音机上。
老收音机无疑是我们儿时最贵重的电器。它的到来,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见识,使我们的视野远远地延伸到了小镇之外,知道在小镇的外面还有一个炫丽多彩的世界。记得上小学的那些日子里,每天下午放学回到家里,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放下书包,搬来小木凳端端正正地坐在收音机前,然后眼巴巴地望着墙壁上的挂钟,瞅着指针指到6点钟时,便迫不急待地打开收音机。随着收音机里传出那熟悉的声音“嘀嘀嗒,嘀嘀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我们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欢喜和激动了……
而在中午12点至12点半,又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时间。“千里走单骑”“火烧连营”“虎牢关”“蒋干盗书”“辕门射戟”——这一个个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最初我就是从老收音机里听到的。老收音机,见证了我的懵懂童年少年,也陪伴着我一路成长。
针线筐、红木箱、收音机,母亲的这些老物件,在我心里从未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