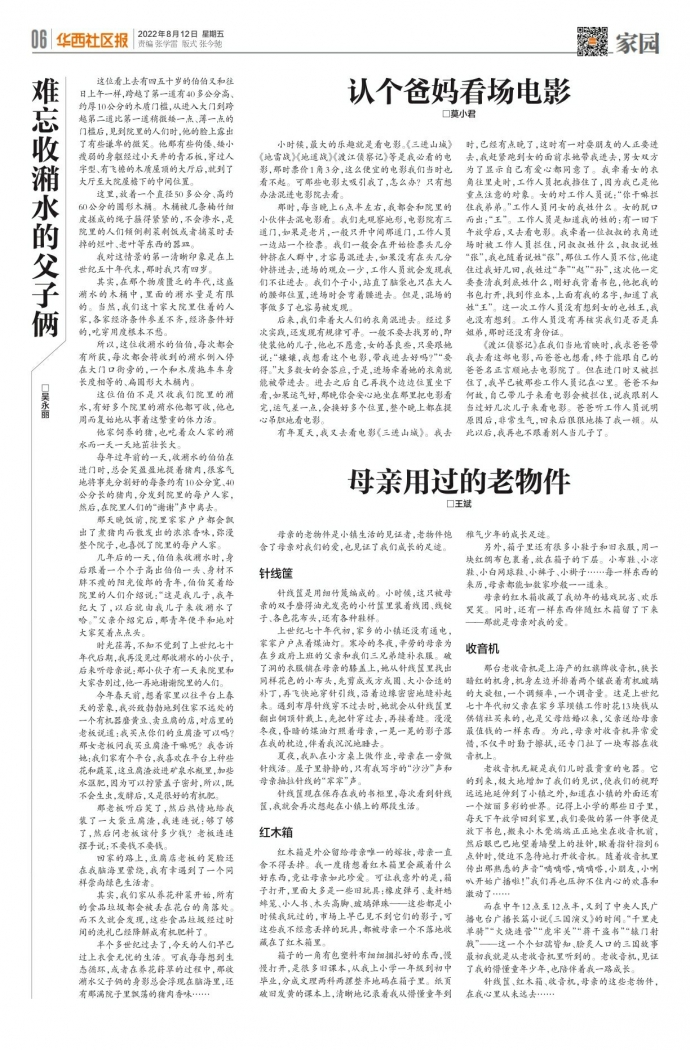难忘收潲水的父子俩
□吴永丽
这位看上去有四五十岁的伯伯又和往日上午一样,跨越了第一道有40多公分高、约厚10公分的木质门槛,从进入大门到跨越第二道比第一道稍微矮一点、薄一点的门槛后,见到院里的人们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有些谦卑的微笑。他那有些佝偻、矮小瘦弱的身躯经过小天井的青石板,穿过人字型、有飞檐的木质屋顶的大厅后,就到了大厅至大院屋檐下的中间位置。
这里,放着一个直径50多公分、高约60公分的圆形木桶。木桶被几条楠竹细皮搓成的绳子箍得紧紧的,不会渗水,是院里的人们倾倒剩菜剩饭或者摘菜时丢掉的烂叶、老叶等东西的器皿。
我对这情景的第一清晰印象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时我只有四岁。
其实,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盛潲水的木桶中,里面的潲水量是有限的。当然,我们这十家大院里住着的人家,各家经济条件参差不齐,经济条件好的,吃穿用度根本不愁。
所以,这位收潲水的伯伯,每次都会有所获,每次都会将收到的潲水倒入停在大门口街旁的,一个和木质拖车车身长度相等的、扁圆形大木桶内。
这位伯伯不是只收我们院里的潲水,有好多个院里的潲水他都可收,他也周而复始地从事着这繁重的体力活。
他家饲养的猪,也吃着众人家的潲水而一天一天地茁壮长大。
每年过年前的一天,收潲水的伯伯在进门时,总会笑盈盈地提着猪肉,很客气地将事先分割好的每条约有10公分宽、40公分长的猪肉,分发到院里的每户人家,然后,在院里人们的“谢谢”声中离去。
那天晚饭前,院里家家户户都会飘出了煮猪肉而散发出的浓浓香味,弥漫整个院子,也喜悦了院里的每户人家。
几年后的一天,伯伯来收潲水时,身后跟着一个个子高出伯伯一头、身材不胖不瘦的阳光俊郎的青年,伯伯笑着给院里的人们介绍说:“这是我儿子,我年纪大了,以后就由我儿子来收潲水了哈。”父亲介绍完后,那青年便平和地对大家笑着点点头。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再没见过那收潲水的小伙子,后来听母亲说:那小伙子有一天来院里和大家告别过,他一再地谢谢院里的人们。
今年春天前,想着家里以往平台上春天的景象,我兴致勃勃地到住家不远处的一个有机器磨黄豆、卖豆腐的店,对店里的老板说道:我买点你们的豆腐渣可以吗?那女老板问我买豆腐渣干嘛呢?我告诉她:我们家有个平台,我喜欢在平台上种些花和蔬菜,这豆腐渣放进矿泉水瓶里,加些水沤肥,因为可以拧紧盖子密封,所以,既不会生虫,发酵后,又是很好的有机肥。
那老板听后笑了,然后热情地给我装了一大袋豆腐渣,我连连说:够了够了,然后问老板该付多少钱?老板连连摆手说:不要钱不要钱。
回家的路上,豆腐店老板的笑脸还在我脑海里萦绕,我有幸遇到了一个同样崇尚绿色生活者。
其实,我们家从养花种菜开始,所有的食品垃圾都会被丢在花台的角落处。而不久就会发现,这些食品垃圾经过时间的洗礼已经降解成有机肥料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人们早已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我每每想到生态循环,或者在养花莳草的过程中,那收潲水父子俩的身影总会浮现在脑海里,还有那满院子里飘荡的猪肉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