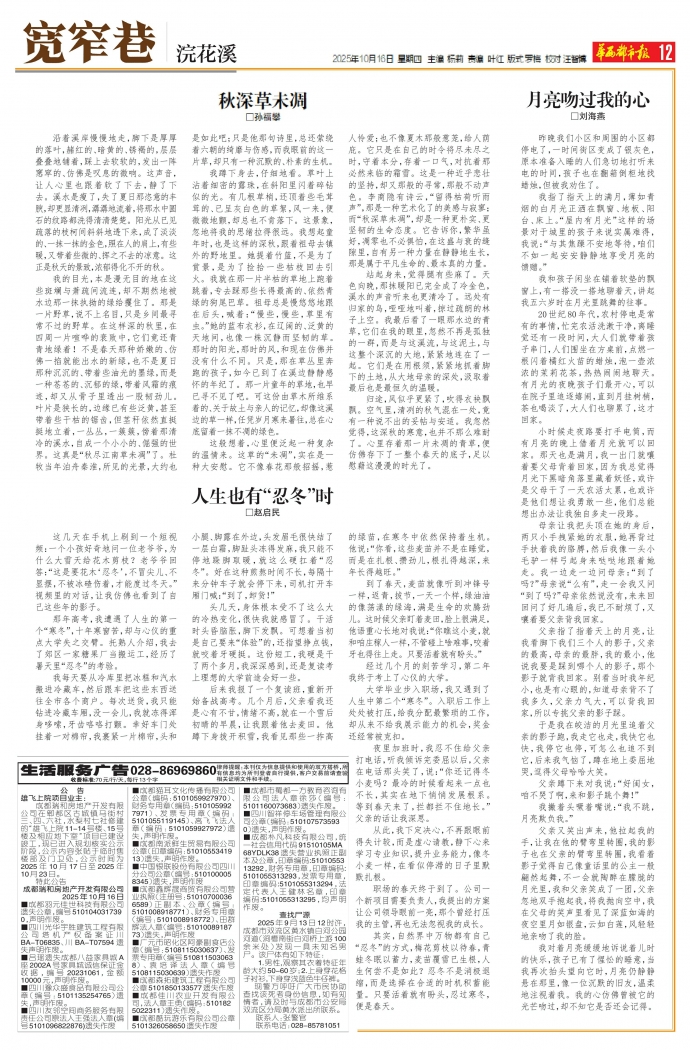秋深草未凋
□孙福攀
沿着溪岸慢慢地走,脚下是厚厚的落叶,赭红的、暗黄的、锈褐的,层层叠叠地铺着,踩上去软软的,发出一阵窸窣的、仿佛是叹息的微响。这声音,让人心里也跟着软了下去,静了下去。溪水是瘦了,失了夏日那恣意的丰腴,却更显清冽,潺潺地流着,将那水中圆石的纹路都洗得清清楚楚。阳光从已见疏落的枝柯间斜斜地透下来,成了淡淡的、一抹一抹的金色,照在人的肩上,有些暖,又带着些微的、挥之不去的凉意。这正是秋天的景致,浓郁得化不开的秋。
我的目光,本是漫无目的地在这些斑斓与萧疏间流连,却不期然地被水边那一抹执拗的绿给攫住了。那是一片野草,说不上名目,只是乡间最寻常不过的野草。在这样深的秋里,在四周一片喧哗的衰败中,它们竟还青青地绿着!不是春天那种娇嫩的、仿佛一掐就能出水的新绿,也不是夏日那种沉沉的、带着些油光的墨绿,而是一种苍苍的、沉郁的绿,带着风霜的痕迹,却又从骨子里透出一股韧劲儿。叶片是狭长的,边缘已有些泛黄,甚至带着些干枯的锯齿,但茎秆依然直挺挺地立着,一丛丛,一簇簇,傍着那清冷的溪水,自成一个小小的、倔强的世界。这真是“秋尽江南草未凋”了。杜牧当年泊舟秦淮,所见的光景,大约也是如此吧;只是他那句诗里,总还萦绕着六朝的绮靡与伤感,而我眼前的这一片草,却只有一种沉默的、朴素的生机。
我蹲下身去,仔细地看。草叶上沾着细密的露珠,在斜阳里闪着碎钻似的光。有几根草梢,还顶着些毛茸茸的、已呈灰白色的草絮,风一来,便微微地颤,却总也不肯落下。这景象,忽地将我的思绪拉得很远。我想起童年时,也是这样的深秋,跟着祖母去镇外的野地里。她提着竹篮,不是为了赏景,是为了捡拾一些枯枝回去引火。我就在那一片半枯的草地上跑着跳着,专去踩那些长得最高的、依然青绿的狗尾巴草。祖母总是慢悠悠地跟在后头,喊着:“慢些,慢些,草里有虫。”她的蓝布衣衫,在辽阔的、泛黄的天地间,也像一株沉静而坚韧的草。那时的阳光,那时的风,和现在仿佛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那在草丛里奔跑的孩子,如今已到了在溪边静静感怀的年纪了。那一片童年的草地,也早已寻不见了吧。可这份由草木所维系着的、关于故土与亲人的记忆,却像这溪边的草一样,任凭岁月寒来暑往,总在心底留着一抹不凋的绿色。
这般想着,心里便泛起一种复杂的温情来。这草的“未凋”,实在是一种大安慰。它不像春花那般招摇,惹人怜爱;也不像夏木那般葱茏,给人荫庇。它只是在自己的时令将尽未尽之时,守着本分,存着一口气,对抗着那必然来临的霜雪。这是一种近乎悲壮的坚持,却又那般的寻常,那般不动声色。李商隐有诗云,“留得枯荷听雨声”,那是一种艺术化了的美感与寂寥;而“秋深草未凋”,却是一种更朴实、更坚韧的生命态度。它告诉你,繁华虽好,凋零也不必惧怕,在这盛与衰的缝隙里,自有另一种力量在静静地生长,那是属于平凡生命的、最本真的力量。
站起身来,觉得腿有些麻了。天色向晚,那抹暖阳已完全成了冷金色,溪水的声音听来也更清冷了。远处有归家的鸟,哑哑地叫着,掠过疏朗的林子上空。我最后看了一眼那水边的青草,它们在我的眼里,忽然不再是孤独的一群,而是与这溪流,与这泥土,与这整个深沉的大地,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它们是在用根须,紧紧地抓着脚下的土地,从大地母亲的深处,汲取着最后也是最恒久的温暖。
归途,风似乎更紧了,吹得衣袂飘飘。空气里,清冽的秋气混在一处,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妥帖与安适。我忽然觉得,这深秋的寒意,也并不那么难耐了。心里存着那一片未凋的青草,便仿佛存下了一整个春天的底子,足以慰藉这漫漫的时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