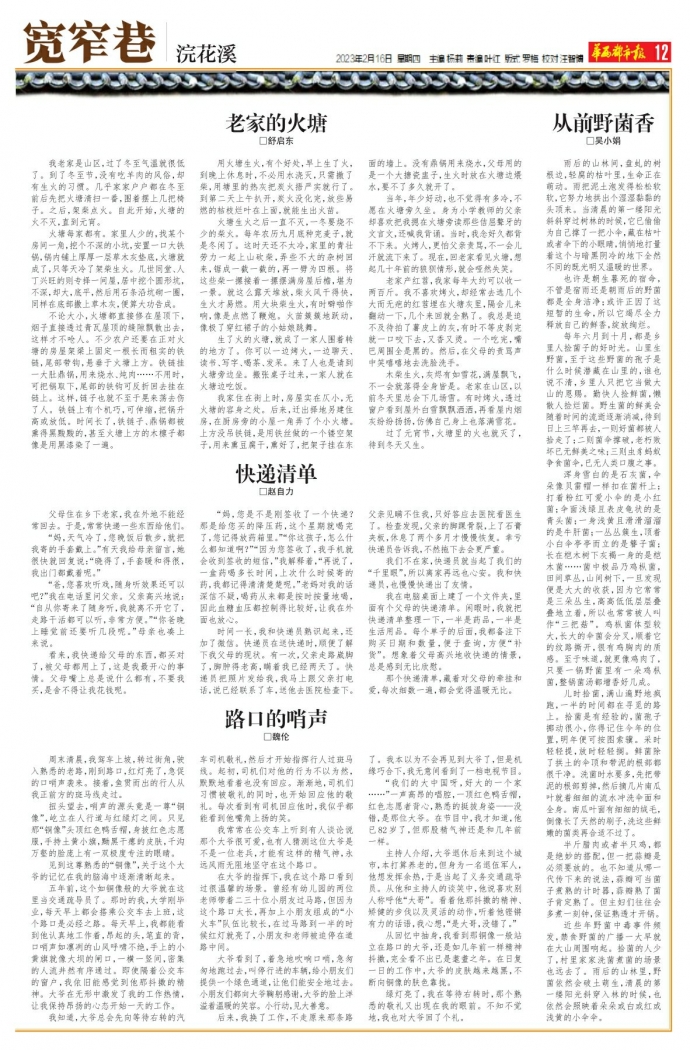老家的火塘
□舒启东
我老家是山区,过了冬至气温就很低了。到了冬至节,没有吃羊肉的风俗,却有生火的习惯。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冬至前后先把火塘清扫一番,围着摆上几把椅子。之后,架柴点火。自此开始,火塘的火不灭,直到元宵。
火塘每家都有。家里人少的,找某个房间一角,挖个不深的小坑,安置一口大铁锅,锅内铺上厚厚一层草木灰垫底,火塘就成了,只等天冷了架柴生火。几世同堂、人丁兴旺的则专择一间屋,居中挖个圆形坑,不深,却大,底平,然后用石条沿坑砌一圈,同样在底部撒上草木灰,便算大功告成。
不论大小,火塘都直接修在屋顶下,烟子直接透过青瓦屋顶的缝隙飘散出去,这样才不呛人。不少农户还要在正对火塘的房屋架梁上固定一根长而粗实的铁链,尾部带钩,悬垂于火塘上方。铁链挂一大肚鼎锅,用来烧水、炖肉……不用时,可把锅取下,尾部的铁钩可反折回去挂在链上。这样,链子也就不至于晃来荡去伤了人。铁链上有个机巧,可伸缩,把锅升高或放低。时间长了,铁链子、鼎锅都被熏得黑黢黢的,甚至火塘上方的木檩子都像是用黑漆染了一遍。
用火塘生火,有个好处,早上生了火,到晚上休息时,不必用水浇灭,只需撤了柴,用塘里的热灰把炭火捂严实就行了。到第二天上午扒开,炭火没化完,放些易燃的枯枝烂叶在上面,就能生出火苗。
火塘生火之后一直不灭,一冬要烧不少的柴火。每年农历九月底种完麦子,就是冬闲了。这时天还不太冷,家里的青壮劳力一起上山砍柴,弄些不大的杂树回来,锯成一截一截的,再一劈为四根。将这些柴一摞接着一摞摆满房屋后檐,堪为一景。就这么露天堆放,柴火风干得快,生火才易燃。用大块柴生火,有时噼啪作响,像是点燃了鞭炮。火苗簇簇地跃动,像极了穿红裙子的小姑娘跳舞。
生了火的火塘,就成了一家人围着转的地方了。你可以一边烤火,一边聊天、读书、写字、喝茶、发呆。来了人也是请到火塘旁边坐。搬张桌子过来,一家人就在火塘边吃饭。
我家住在街上时,房屋实在仄小,无火塘的容身之处。后来,迁出择地另建住房,在厨房旁的小屋一角弄了个小火塘。上方没吊铁链,是用铁丝做的一个镂空架子,用来熏豆腐干,熏好了,把架子挂在东面的墙上。没有鼎锅用来烧水,父母用的是一个大搪瓷盅子,生火时放在火塘边煨水,要不了多久就开了。
当年,年少好动,也不觉得有多冷,不愿在火塘旁久坐。身为小学教师的父亲却喜欢把我摁在火塘旁读那些佶屈聱牙的文言文,还喊我背诵。当时,我念好久都背不下来。火烤人,更怕父亲责骂,不一会儿汗就流下来了。现在,回老家看见火塘,想起几十年前的狼狈情形,就会哑然失笑。
老家产红苕,我家每年大约可以收一两百斤。我不喜欢烤火,却经常去选几个大而无疤的红苕埋在火塘灰里,隔会儿来翻动一下,几个来回就全熟了。我总是迫不及待拍了薯皮上的灰,有时不等皮剥完就一口咬下去,又香又烫。一个吃完,嘴巴周围全是黑的。然后,在父母的责骂声中笑嘻嘻地去洗脸洗手。
木柴生火,灰烬有如雪花,满屋飘飞,不一会就落得全身皆是。老家在山区,以前冬天里总会下几场雪。有时烤火,透过窗户看到屋外白雪飘飘洒洒,再看屋内烟灰纷纷扬扬,仿佛自己身上也落满雪花。
过了元宵节,火塘里的火也就灭了,待到冬天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