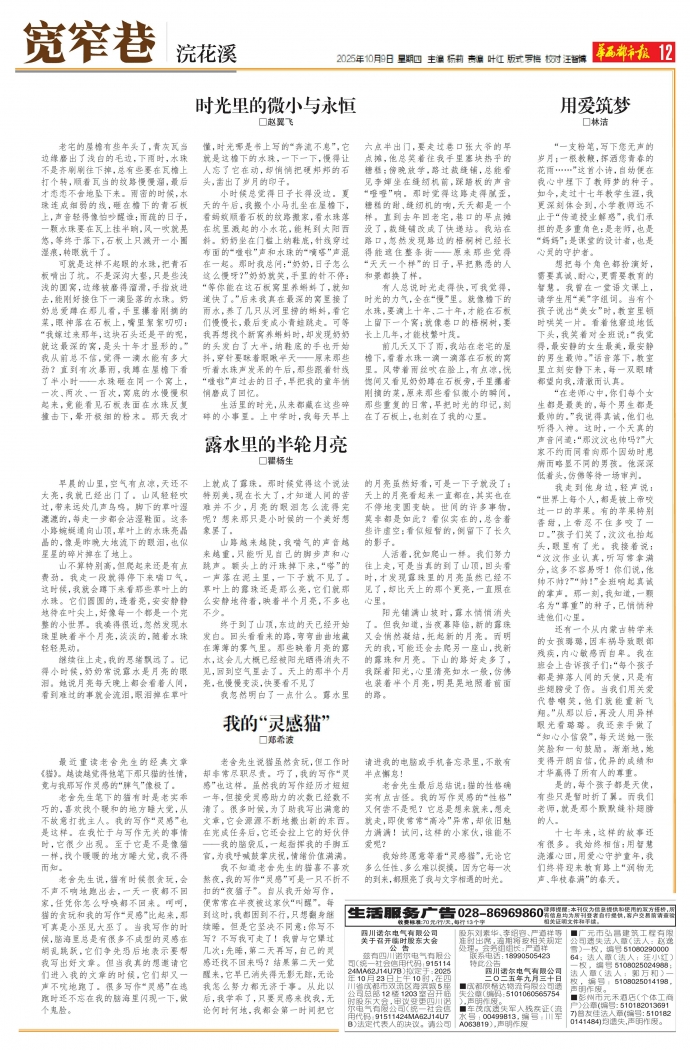时光里的微小与永恒
□赵翼飞
老宅的屋檐有些年头了,青灰瓦当边缘磨出了浅白的毛边,下雨时,水珠不是齐刷刷往下掉,总有些要在瓦檐上打个转,顺着瓦当的纹路慢慢溜,最后才恋恋不舍地坠下来。雨密的时候,水珠连成细弱的线,砸在檐下的青石板上,声音轻得像怕吵醒谁;雨疏的日子,一颗水珠要在瓦上挂半晌,风一吹就晃悠,等终于落下,石板上只溅开一小圈湿痕,转眼就干了。
可就是这样不起眼的水珠,把青石板啃出了坑。不是深沟大壑,只是些浅浅的圆窝,边缘被磨得溜滑,手指放进去,能刚好接住下一滴坠落的水珠。奶奶总爱蹲在那儿看,手里攥着刚摘的菜,眼神落在石板上,嘴里絮絮叨叨:“我嫁过来那年,这块石头还是平的呢,就这最深的窝,是头十年才显形的。”我从前总不信,觉得一滴水能有多大劲?直到有次暴雨,我蹲在屋檐下看了半小时——水珠砸在同一个窝上,一次、两次、一百次,窝底的水慢慢积起来,竟能看见石板表面在水珠反复撞击下,晕开极细的粉末。那天我才懂,时光哪是书上写的“奔流不息”,它就是这檐下的水珠,一下一下,慢得让人忘了它在动,却悄悄把硬邦邦的石头,凿出了岁月的印子。
小时候总觉得日子长得没边。夏天的午后,我搬个小马扎坐在屋檐下,看蚂蚁顺着石板的纹路搬家,看水珠落在坑里溅起的小水花,能耗到太阳西斜。奶奶坐在门槛上纳鞋底,针线穿过布面的“嗤啦”声和水珠的“嘀嗒”声混在一起。那时我总问:“奶奶,日子怎么这么慢呀?”奶奶就笑,手里的针不停:“等你能在这石板窝里养蝌蚪了,就知道快了。”后来我真在最深的窝里接了雨水,养了几只从河里捞的蝌蚪,看它们慢慢长,最后变成小青蛙跳走。可等我再想找个新窝养蝌蚪时,却发现奶奶的头发白了大半,纳鞋底的手也开始抖,穿针要眯着眼瞅半天——原来那些听着水珠声发呆的午后,那些跟着针线“嗤啦”声过去的日子,早把我的童年悄悄磨成了回忆。
生活里的时光,从来都藏在这些碎碎的小事里。上中学时,我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要走过巷口张大爷的早点摊,他总笑着往我手里塞块热乎的糖糕;傍晚放学,路过裁缝铺,总能看见李婶坐在缝纫机前,踩踏板的声音“噔噔”响。那时觉得这路走得腻歪,糖糕的甜、缝纫机的响,天天都是一个样。直到去年回老宅,巷口的早点摊没了,裁缝铺改成了快递站。我站在路口,忽然发现路边的梧桐树已经长得能遮住整条街——原来那些觉得“天天一个样”的日子,早把熟悉的人和景都换了样。
有人总说时光走得快,可我觉得,时光的力气,全在“慢”里。就像檐下的水珠,要滴上十年、二十年,才能在石板上留下一个窝;就像巷口的梧桐树,要长上几年,才能枝繁叶茂。
前几天又下了雨,我站在老宅的屋檐下,看着水珠一滴一滴落在石板的窝里。风带着雨丝吹在脸上,有点凉,恍惚间又看见奶奶蹲在石板旁,手里攥着刚摘的菜,原来那些看似微小的瞬间,那些重复的日常,早把时光的印记,刻在了石板上,也刻在了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