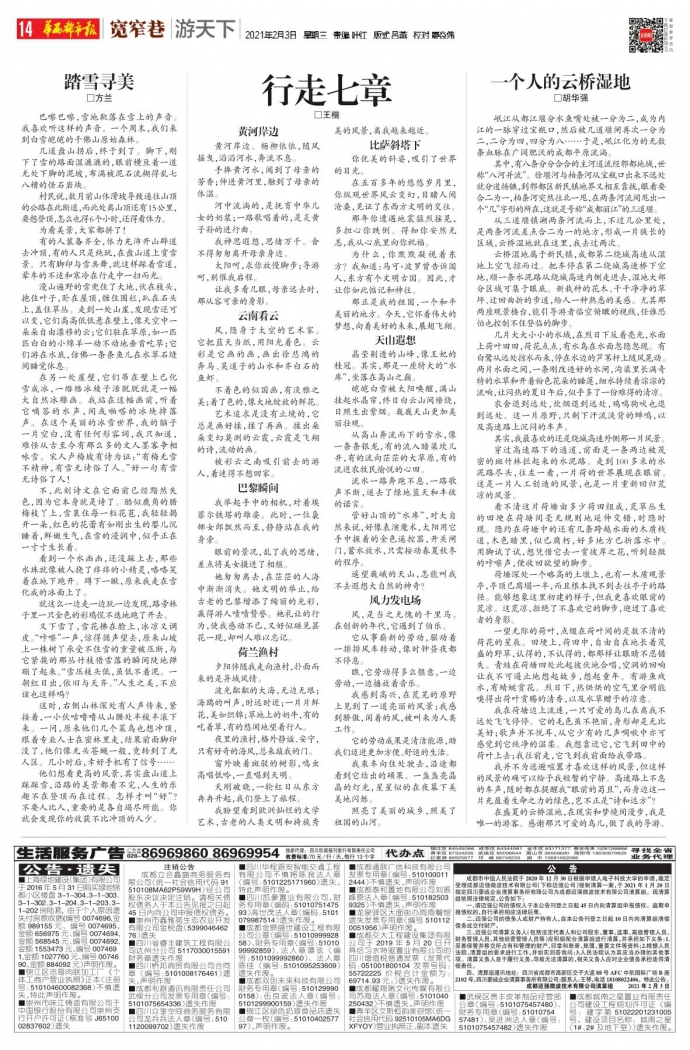张问陶家族的山东情缘(下)
张问陶画作《四喜图》。
张问陶书法作品。
山东莱州风景秀丽。
□庞惊涛
应该说,张问陶对山东的感情是很深的,他自 认 生 是“齐人”——今天的“蜀人”不免会为此吃点飞醋。他自小惯 听 惯 说“齐语”,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因此,他对这一片热土魂牵梦绕也好理解。而对四 川 遂 宁呢,因为居住时间少,多少有些近乡情怯,第一次回遂宁时,他已经是二十三岁的青年了。《初归遂宁作》里写道:“北马南船笑此身,归来已是廿年人。敝庐乍到翻疑客,破砚相随不救贫。”正是这种疏淡中有兴奋、感叹、自我安慰等复杂感情的真实写照。
一边是山东、一边是四川,在张 问 陶 心中,两个地方的情感很难分出高低轻重。我们只 是 经 由“一门四世宦山东”这句诗,考察出张问陶家族与山东的特别情缘:因仕宦而结下的地缘既安顿了一个家族庞大的人口,而这种地缘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家族中人的仕宦和人生,尤其是张问陶的人生。
写给遂宁的诗歌不少
对山东的情感也很深
山东莱州是张问陶仕途的最后一站。
他从莱州辞官后,计划回到家乡遂宁养老。“自惭五十枉知非,万里思亲却未归。”(《闻李松云前辈调任成都寄怀有作》)说的就是这个计划,但苦于旅资不足,不得不暂寄苏州。不意到苏州后病情加重,不久病逝于苏州寓所。无论是乡籍遂宁还是生地山东馆陶,他都没有机会再亲近了。人生怅恨,每每如此。
张问陶一生,籍在四川遂宁,生在山东馆陶,成都是中转站,京城是宦游地,莱州是他仕途的最后一站,苏州呢,是他生命的最后一站。除了羁旅行游,一生所经停处,不过这几处。
对四川,他既陌生,又向往。二十三岁那年回家,极目所见,故乡山清水秀,风韵独具。此后少有的几次回家,他遍访家乡名胜古迹,如广德寺、灵泉寺,都有诗题咏。宦游中,他总恨自己“不及帘前双燕子,年年来绕故园花”(家居感兴》),而最后老病未能归,则是他最大的恨事了。
从数量上来看,他写给遂宁的诗歌不少,超过了在山东的诗作。以《出守东莱集》作为对山东题咏的观察入口,他对四川遂宁的感情似乎要深于山东。但细细读他的《药庵退守集》中涉及山东的诗作,发现他对山东的感情也可以说是山高海深。
在一首诗里,他感叹说:“弹指百年冠盖影,孙曾才过又玄孙。”诗中自注云:先祖守登州,先君令馆陶,予复守莱郡。说的都是张家和山东特别的情缘。
还有一句说:“却向山东留故实,莱州太守兖州人。”他人走了,但是会留下很多他在山东的故事,“我这个莱州太守,应该可以说是兖州人吧”。
秉持豁达天下观
自觉担负报国使命
“处处留情处处情”,像张问陶这样诗主性灵的人,对人对地方是最易生感情的。不虚应、不蹈空,一切发自肺腑,诗文所见,都是真情实感,所以山东和四川的情感摆位,对诗人而言都是一样的重要。
这当然还关涉到他通达的天下观:一生行迹主要在山东、四川和京城之间,在并不长的人生长度里,得以构建起比较开放的天下观。空间理论上,受时代局限,张问陶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还没有能力构建起完全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仍以中国为中心,所以中华大地,哪里都可以是寄情之地。同时,他这个家族的为政者,从张鹏翮到他这一辈,无论官做得大还是小,都没有很强的地方乡党概念,而在俗务上,也让他们减少了很多无谓的交际应酬,得以安持于文教事业和著书立说。
从张鹏翮开始,尽管家族落籍四川遂宁,但因为有儒家“为万世开太平”的教化,便自觉担负起了以身报国的使命。所以,不管山长水阔、天远地远,必须从遂宁或馆陶一隅,走向国家的政治中心。
这让我再一次想到张船山的后人、被誉为世界级华裔学术大师之一的张隆溪先生的天下观:他虽有成都情结,但更有放眼四海的开放观念,也从不以“张问陶后人”而自得。在一次采访复函中,他坦言,从成都走出去后,他“更觉世界之大,天下之广”“对一个人的眼光和胸怀更为重要”。可谓有其祖必有其后人。
从遂宁到京城,再到山东,张船山走了五十一年。他离开后的两百多年,他的诗文及其精神世界,又从遂宁、从山东走向了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