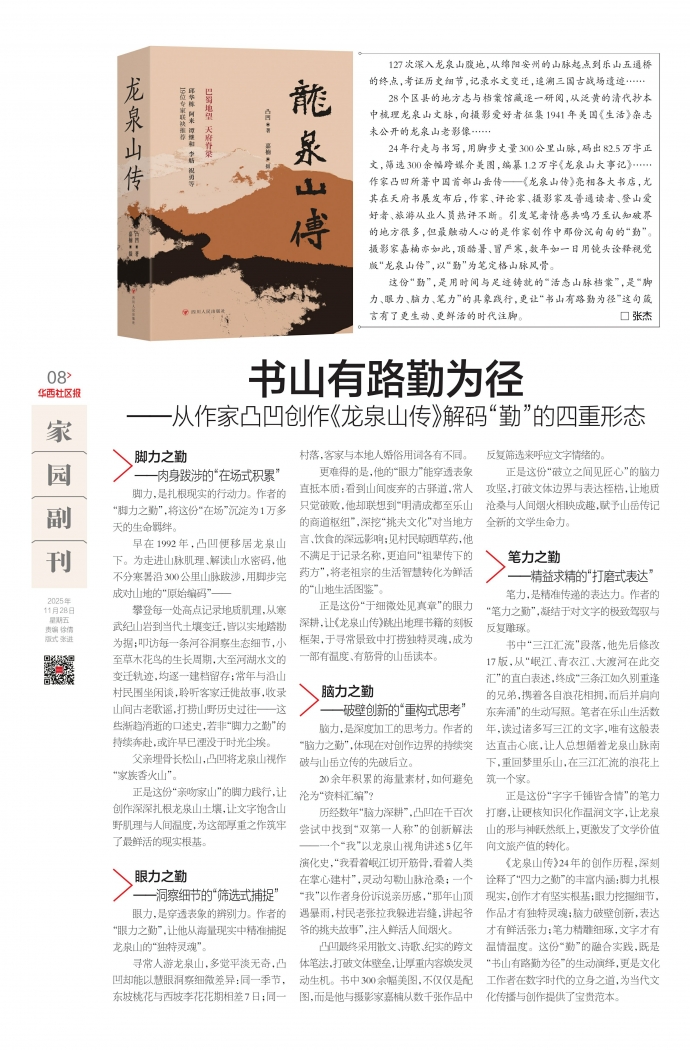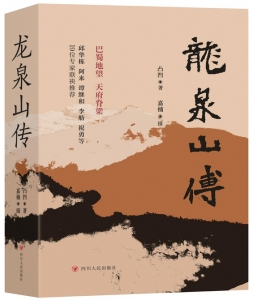书山有路勤为径
——从作家凸凹创作《龙泉山传》解码“勤”的四重形态
127次深入龙泉山腹地,从绵阳安州的山脉起点到乐山五通桥的终点,考证历史细节,记录水文变迁,追溯三国古战场遗迹……
28个区县的地方志与档案馆藏逐一研阅,从泛黄的清代抄本中梳理龙泉山文脉,向摄影爱好者征集1941年美国《生活》杂志未公开的龙泉山老影像……
24年行走与书写,用脚步丈量300公里山脉,码出82.5万字正文,筛选300余幅跨媒介美图,编纂1.2万字《龙泉山大事记》……作家凸凹所著中国首部山岳传——《龙泉山传》亮相各大书店,尤其在天府书展发布后,作家、评论家、摄影家及普通读者、登山爱好者、旅游从业人员热评不断。引发笔者情感共鸣乃至认知破界的地方很多,但最触动人心的是作家创作中那份沉甸甸的“勤”。摄影家嘉楠亦如此,顶酷暑、冒严寒,数年如一日用镜头诠释视觉版“龙泉山传”,以“勤”为笔定格山脉风骨。
这份“勤”,是用时间与足迹铸就的“活态山脉档案”,是“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具象践行,更让“书山有路勤为径”这句箴言有了更生动、更鲜活的时代注脚。 □张杰
脚力之勤
——肉身跋涉的“在场式积累”
脚力,是扎根现实的行动力。作者的“脚力之勤”,将这份“在场”沉淀为1万多天的生命羁绊。
早在1992年,凸凹便移居龙泉山下。为走进山脉肌理、解读山水密码,他不分寒暑沿300公里山脉跋涉,用脚步完成对山地的“原始编码”——
攀登每一处高点记录地质肌理,从寒武纪山岩到当代土壤变迁,皆以实地踏勘为据;叩访每一条河谷洞察生态细节,小至草木花鸟的生长周期,大至河湖水文的变迁轨迹,均逐一建档留存;常年与沿山村民围坐闲谈,聆听客家迁徙故事,收录山间古老歌谣,打捞山野历史过往——这些渐趋消逝的口述史,若非“脚力之勤”的持续奔赴,或许早已湮没于时光尘埃。
父亲埋骨长松山,凸凹将龙泉山视作“家族香火山”。
正是这份“亲吻家山”的脚力践行,让创作深深扎根龙泉山土壤,让文字饱含山野肌理与人间温度,为这部厚重之作筑牢了最鲜活的现实根基。
眼力之勤
——洞察细节的“筛选式捕捉”
眼力,是穿透表象的辨别力。作者的“眼力之勤”,让他从海量现实中精准捕捉龙泉山的“独特灵魂”。
寻常人游龙泉山,多觉平淡无奇,凸凹却能以慧眼洞察细微差异:同一季节,东坡桃花与西坡李花花期相差7日;同一村落,客家与本地人婚俗用词各有不同。
更难得的是,他的“眼力”能穿透表象直抵本质:看到山间废弃的古驿道,常人只觉破败,他却联想到“明清成都至乐山的商道枢纽”,深挖“挑夫文化”对当地方言、饮食的深远影响;见村民晾晒草药,他不满足于记录名称,更追问“祖辈传下的药方”,将老祖宗的生活智慧转化为鲜活的“山地生活图鉴”。
正是这份“于细微处见真章”的眼力深耕,让《龙泉山传》跳出地理书籍的刻板框架,于寻常景致中打捞独特灵魂,成为一部有温度、有筋骨的山岳读本。
脑力之勤
——破壁创新的“重构式思考”
脑力,是深度加工的思考力。作者的“脑力之勤”,体现在对创作边界的持续突破与山岳立传的先破后立。
20余年积累的海量素材,如何避免沦为“资料汇编”?
历经数年“脑力深耕”,凸凹在千百次尝试中找到“双第一人称”的创新解法——一个“我”以龙泉山视角讲述5亿年演化史,“我看着岷江切开筋骨,看着人类在掌心建村”,灵动勾勒山脉沧桑;一个“我”以作者身份诉说亲历感,“那年山顶遇暴雨,村民老张拉我躲进岩缝,讲起爷爷的挑夫故事”,注入鲜活人间烟火。
凸凹最终采用散文、诗歌、纪实的跨文体笔法,打破文体壁垒,让厚重内容焕发灵动生机。书中300余幅美图,不仅仅是配图,而是他与摄影家嘉楠从数千张作品中反复筛选来呼应文字情绪的。
正是这份“破立之间见匠心”的脑力攻坚,打破文体边界与表达桎梏,让地质沧桑与人间烟火相映成趣,赋予山岳传记全新的文学生命力。
笔力之勤
——精益求精的“打磨式表达”
笔力,是精准传递的表达力。作者的“笔力之勤”,凝结于对文字的极致驾驭与反复雕琢。
书中“三江汇流”段落,他先后修改17版,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在此交汇”的直白表述,终成“三条江如久别重逢的兄弟,携着各自浪花相拥,而后并肩向东奔涌”的生动写照。笔者在乐山生活数年,读过诸多写三江的文字,唯有这般表达直击心底,让人总想循着龙泉山脉南下,重回梦里乐山,在三江汇流的浪花上筑一个家。
正是这份“字字千锤皆含情”的笔力打磨,让硬核知识化作温润文字,让龙泉山的形与神跃然纸上,更激发了文学价值向文旅产值的转化。
《龙泉山传》24年的创作历程,深刻诠释了“四力之勤”的丰富内涵:脚力扎根现实,创作才有坚实根基;眼力挖掘细节,作品才有独特灵魂;脑力破壁创新,表达才有鲜活张力;笔力精雕细琢,文字才有温情温度。这份“勤”的融合实践,既是“书山有路勤为径”的生动演绎,更是文化
工作者在数字时代的立身之道,为当代文化传播与创作提供了宝贵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