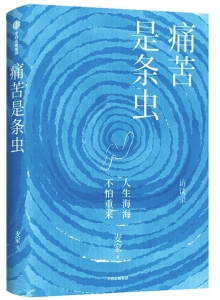作家麦家自我“解密”:
痛苦是条虫潜伏于心
麦家新书《痛苦是条虫》出版社供图
麦家吴德玉摄
作为作家,麦家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作品被译为三十四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其中《解密》《暗算》入选“企鹅经典”文库。《解密》被翻译成30种语言,是世界图书馆收藏量第一的中文作品,被《经济学人》评为“2014年度全球十大小说”;《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如此漂亮的成绩单背后,麦家却说,痛苦和矛盾像一条虫,潜伏在他的内心深处,成为他生命的底色。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天生是个作家,因为我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心中有淤泥要疏浚,写作是我的命,也是渡我的桨。但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并不配当作家,因为我写一本书是那么难,总是殚精竭虑,颠来倒去推敲、修改,又不免胎死腹中:这样的惩罚像季节一样更替不止。”在新书《痛苦是条虫》里,麦家将“解密”的方向,对准自己。
2025年8月,麦家回到成都,牵着年幼女儿的手,来了一场文学寻亲之旅。第一站是一环路上一家开了很多年的电影院。他说这里是他的“私人电影院”,“一方面以前经常来看电影,老板是我多年非常要好的朋友。更重要的是,电影《风声》最先在这里点映,取得很好的票房。可以说,这是我的谍战小说开始飞翔的地方。”在这家影院,麦家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他一如既往地真诚,谈到母亲,情难自已,一度哽咽流泪。
帮他修复与故乡的关系:“母亲是我生命的托底人”
近日,麦家访谈录《痛苦是条虫》由中信出版社推出。书中收纳了包括王德威、何平、季进、季亚娅、姜广平、骆以军等在内的华语世界资深评论家、出版人、作家跟麦家展开对谈的实录。在八篇深度对话中,麦家全盘托出他早年的成长经历,并透露了他从“谍战三部曲”书写特殊人物转向“故乡三部曲”讲述普通人故事的心理轨迹。这一次,麦家“解密”他自己。
麦家的童年充满被欺凌的记忆,这让他与家乡多年保持距离。他在外求学、工作、生活,远离故土,文学上也不碰相关题材。但近些年来,他回到故乡生活,开始写故乡主题的作品。这一切,都跟他的母亲密切相关——是坚强乐观善良的母亲帮助儿子修复与故乡的关系。麦家说:“有一天,母亲发现我还在记恨小时候欺负我们的人,她大吃一惊,说你读了那么多书,跑了那么多码头,怎么还会放不下以前这些事情?早该放下了。我母亲当年比我遭受的委屈更深,她却比我早就放下。在我的印象中,母亲这么多年确实对每一个人都尽量笑脸以对。我母亲是一个太了不起的人。像我这样经历和性格的人,很容易变成一个坏孩子或者废物,但是母亲为我托了底。”
麦家笔下塑造了很多美好的女性,像《暗算》里的黄依依,《人间信》里的奶奶、外婆等。麦家说:“虽然不是刻意的,但仔细分析一下,她们的性格底色跟我的母亲都有分不开的联系。母亲让我对女性有一种仰慕。”
唯一的虚荣心:“读者喜欢并能看懂我的小说”
麦家的很多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收入不菲,但金钱带来的快乐满足不了他,“我想要的是导演和制作团队能够看懂我的小说,能够把我小说的精髓表达出来。我相信我的小说对人性有一些个性的思考,这种思考被人接受远比挣到金钱更让我满足。我真的不在乎金钱,其实我在没钱的时候,在《解密》17次被退稿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用金钱来捍卫自己的尊严。我一直有个虚荣心,现在仅剩的虚荣心,就是读者喜欢并能看懂我的小说,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在麦家的文学之路上,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博尔赫斯。用麦家自己的话来说,“若没有博尔赫斯,可能也没有我现在的一系列小说。”一般来说,谍战或者特情被视为通俗文学题材。作为有志于在所谓的纯文学、严肃文学里面“打江山”的人,麦家一开始不屑于写通俗文学。但读到博尔赫斯的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麦家得到很大的启发,“这部小说写的就是一个间谍故事。博尔赫斯可是公认的‘作家中的作家’,他很纯粹,一点杂质没有,纯得像水晶一样,可人家照样在写盗马贼,写侦探小说。我突然懂得,写什么无所谓,关键看你怎么写。”
对话编故事不是作家的强项写小说时不要想着影视改编
记者:你经常夸成都这个城市很特别,对你有非一般的意义。那每次回到成都,会不会让你感到内心的温度高一些,开心快乐一些?
麦家:
对我而言,成都确实是非常特别的存在。每次回来,我一下飞机,车子从机场驶入市区,我都能感受到这种特别。我会看到很多人的面部表情是充满自信的,有松弛感。我也会特别提醒我太太注意这一点,这个地方的人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
记者:在四川生活多年,你会说四川话吗?
麦家
:我在四川生活的那些年,基本不说四川话。因为我生活和工作环境都是普通话环境。但奇妙的是,当我离开四川以后,我竟然开始喜欢说四川话了。看电影《让子弹飞》,我特别喜欢看川话版。而且,我在四川那些年很少吃辣,到杭州反而喜欢吃辣了。我这种人,总是会有滞后反应。跟人交往也是这样,经常当时没反应过来。可能是因为离开了四川,反而让我在情感和心理上与它更亲近,我对这个城市有一种深深的爱,当我离开它了,我还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挽留它。
记者:虽然你的新书名字叫《痛苦是条虫》,但现在看你整个人变得比较阳光了。
麦家
:我觉得“阳光”这个词跟我隔绝。我似乎从来就没“阳光”过,一直阴云密布。即使我笑容满面,其实也算不上“阳光”。当然,人的状态会有变化,但底色肯定是不变的。这个底色是由童年经历决定的。哪怕你没意识到,它也会进入你的生命中,成为一种潜意识,成为冰山下面的存在。为什么说“痛苦是条虫”,因为快乐长翅膀会飞走,而痛苦会钻到人的内心深处躲起来。
记者:你是影视化非常成功的作家,对于影视改编有怎样的感想?
麦家
:首先必须得说,影视化能让一部文学作品获得文字难以抵达的受众群。影视化确实给了我巨大的名利回馈。但是话又说回来,一开始写作的时候,心里并没有想到这些作品要改编成影视,我就专心写好小说。以我的观察和经验,如果你写作的时候,试图写得更容易被影视改编,那基本上你不会写好。我以前在电视台工作,当过职业编剧。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和体会就是,导演看中一部小说,往往不是因为你编的故事有多好,而是他被你的文字激发,感到一种气息,一种启发,一种莫名其妙的被吸引的力量。作家千万不要去想着为导演编一个完美的故事,编故事不是作家的强项。只要你把导演的好奇心启发起来了,他会根据你的小说把故事编圆。比如说《解密》里的容金珍,是这个人物闪闪发光,吸引了影视工作者。
记者:《解密》被退稿17次,修改过程长达11年,在这个过程中,你写作的质地和内心的坚强都被提升了。但不得不说,现在这个时代节奏很快,放在现在,11年专注打磨一本书可能不太现实。对于当下有文学创作梦想的年轻人,你会给什么建议?
麦家
:没有人喜欢被压在石头底下11年。我经常想,如果那11年我不是在成都生活,可能早已经垮掉了,成都给我很大的包容和缓冲。这是我个人的故事,也难以被别人复制。我只能说,有时候慢也有好处,太快也不全是好事。《解密》修改很多次才出版,恰好赶上一个它被很好接受的时机。如果它发表很顺利,被传播和接受的效果未必像现在这样好。
记者:从《风声》《暗算》等组成的“谍战系列”到《人生海海》《人间信》等组成的“故乡系列”,你完成了很好的题材转型。接下来的写作大概是什么?
麦家:
我一直计划为母亲写一部纪实作品,只是目前还没动笔。就我的体验来说,纪实性质的作品写作难度要小一些。只要给我时间,慢慢写,一定可以写出来。但是虚构的小说很难写。因为需要平地拔楼,无中生有,需要很大的创造力。每次写小说,我都很紧张,害怕写不出来,或者害怕写得不好。这种害怕,在我写小说的每一天,都陪伴着我。但是让我写母亲,写篇散文,我坐下来就能写,而且很享受写的过程,因为一切都心里有数。我要在自己创造力还旺盛的时候,更多写小说,可能有一天写不动小说之后再去写散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吴德玉雷蕴含实习生罗一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