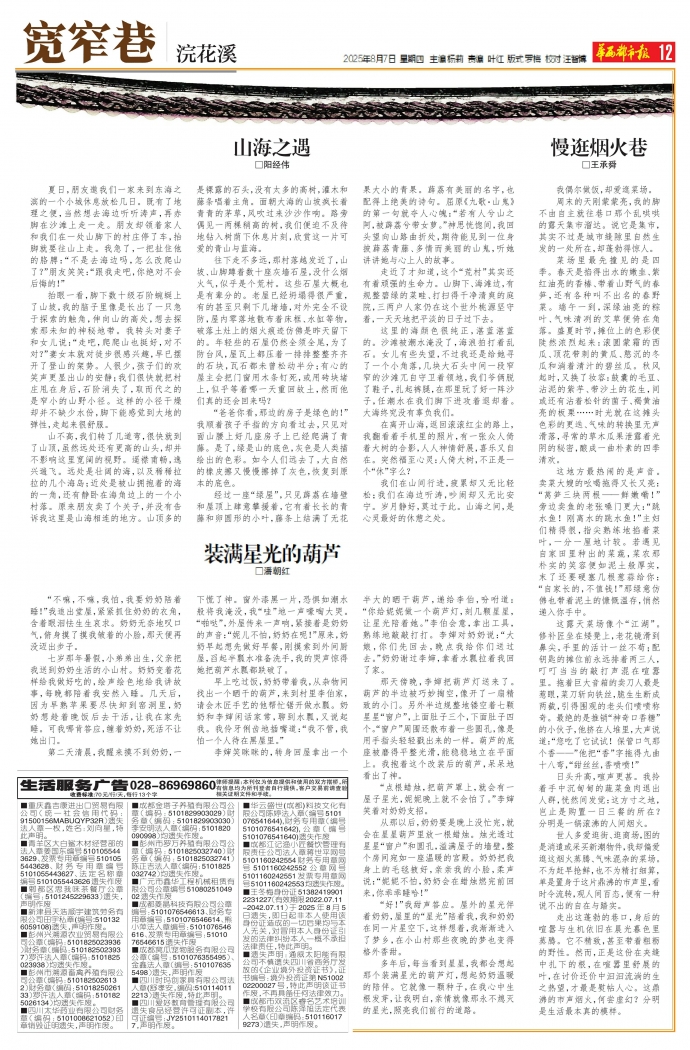山海之遇
□阳经伟
夏日,朋友邀我们一家来到东海之滨的一个小城休息放松几日。既有了地理之便,当然想去海边听听涛声,再赤脚在沙滩上走一走。朋友却领着家人和我们在一处山脚下的村庄停了车,抬脚就要往山上走。我急了,一把扯住他的胳膊:“不是去海边吗,怎么改爬山了?”朋友笑笑:“跟我走吧,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抬眼一看,脚下数十级石阶蜿蜒上了山坡,我的脑子里像是长出了一只急于探索的触角,伸向山的高处,想去探索那未知的神秘地带。我转头对妻子和女儿说:“走吧,爬爬山也挺好,对不对?”妻女本就对徒步很感兴趣,早已摆开了登山的架势。人很少,孩子们的欢笑声更显出山的安静;我们很快就把村庄甩在身后,石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窄小的山野小径。这样的小径干燥却并不缺少水份,脚下能感觉到大地的弹性,走起来很舒服。
山不高,我们转了几道弯,很快就到了山顶,虽然远处还有更高的山头,却并不影响这里宽阔的视野。遥襟甫畅,逸兴遄飞。远处是壮阔的海,以及稀稀拉拉的几个海岛;近处是被山拥抱着的海的一角,还有静卧在海角边上的一个小村落。原来朋友卖了个关子,并没有告诉我这里是山海相连的地方。山顶多的是裸露的石头,没有太多的高树,灌木和藤条唱着主角。面朝大海的山坡疯长着青青的茅草,风吹过来沙沙作响。路旁偶见一两棵稍高的树,我们便迫不及待地钻入树荫下休息片刻,欣赏这一片可爱的青山与蓝海。
往下走不多远,那村落越发近了,山坡、山脚蹲着数十座灰墙石屋,没什么烟火气,似乎是个荒村。这些石屋大概也是有辈分的。老屋已经坍塌得很严重,有的甚至只剩下几堵墙,对外完全不设防,屋内零落地散布着床框、水缸等物,破落土灶上的烟火痕迹仿佛是昨天留下的。年轻些的石屋仍然全须全尾,为了防台风,屋瓦上都压着一排排整整齐齐的石块,瓦石都未曾松动半分;有心的屋主会把门窗用木条钉死,或用砖块堵上,似乎等着哪一天重回故土,然而他们真的还会回来吗?
“爸爸你看,那边的房子是绿色的!”我顺着孩子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对面山腰上好几座房子上已经爬满了青藤。是了,绿是山的底色,灰色是人类描绘出的色彩。如今人们远去了,大自然的橡皮擦又慢慢擦掉了灰色,恢复到原本的底色。
经过一座“绿屋”,只见薜荔在墙壁和屋顶上肆意攀援着,它有着长长的青藤和卵圆形的小叶,藤条上结满了无花果大小的青果。薜荔有美丽的名字,也配得上绝美的诗句。屈原《九歌·山鬼》的第一句就夺人心魄:“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神思恍惚间,我回头望向山路曲折处,期待能见到一位身披薜荔青藤、多情而美丽的山鬼,听她讲讲她与心上人的故事。
走近了才知道,这个“荒村”其实还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山脚下、海滩边,有规整碧绿的菜畦、打扫得干净清爽的庭院,三两户人家仍在这个世外桃源坚守着,一天天地把平淡的日子过下去。
这里的海颜色很纯正,湛蓝湛蓝的。沙滩被潮水淹没了,海浪拍打着乱石。女儿有些失望,不过我还是给她寻了一个小角落,几块大石头中间一段窄窄的沙滩兀自守卫着领地,我们爷俩脱了鞋子,扎起裤腿,在那里玩了好一阵沙子,任潮水在我们脚下进攻着退却着。大海终究没有辜负我们。
在离开山海,返回滚滚红尘的路上,我翻看着手机里的照片,有一张众人倚着大树的合影,人人神情舒展,喜乐又自在。突然福至心灵:人倚大树,不正是一个“休”字么?
我们在山间行进,疲累却又无比轻松;我们在海边听涛,吵闹却又无比安宁。岁月静好,莫过于此。山海之间,是心灵最好的休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