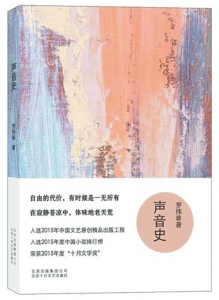“修复人们无法自知的平庸”
罗伟章推出“三史”最后一部《隐秘史》
《隐秘史》
《寂静史》
《声音史》
罗伟章
热爱文学不需要理由,但有一个问题似乎有必要琢磨一下:当下,我们读一部长篇小说的理由是什么?
长篇小说的长度意味着它不大可能不讲故事,但如果仅仅提供一个离奇、精彩的故事,不一定非要读长篇小说。且不说,太阳之下无新事,现在也早已不是狄更斯或者巴尔扎克那样需要通过小说去获得社会知识或者信息的时代。
况且,现在的时间节奏很快。一部长篇的被阅读,意味着要付出足够的耐心、兴趣。最重要的是,作者在提供故事的时候,能否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见识、判断、思考力,以及突出的文笔表现能力。
有耐心有能力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并不少见,但同时有精彩文字表现力的人却不多,因此显得格外珍贵。在当下的小说家群体中,四川作家罗伟章无疑是优秀的一位。
悬疑
只是《隐秘史》的表皮
几年前,罗伟章曾在小说《声音史》里写了一个叫杨浪的人物。他悉心收集着村庄的声音,当那些声音次第消失,他便用自己的天赋异禀模仿那些声音,并借助那些声音让村庄复活。2022年,在新近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书《隐秘史》中,那个村庄依然在,杨浪依然在,而且就是《声音史》里的杨浪,但他已经只是背景了。
在讲故事方面,《隐秘史》比《声音史》走得更远——主框架是一桩凶杀案,一个关于心理隐痛的悬疑故事。桂平昌去山里挖麦冬时,不小心打了个趔趄,由此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洞里深藏已久的秘密随之暴露,这让他瞬间感觉天塌地陷。老婆陈国秀完全没看出桂平昌丢了魂,心性要强的陈国秀早已对自己“软骨头”的男人失望至极,不过她到底发现了异常,于是把男人交给隔壁吴兴贵和陶玉夫妇照顾,自己去镇上开药,等药拿回来……
罗伟章的写作从来都是扎根于最真实、可感的现实,对人物和场景的描写极其逼真,中年夫妻之间的爱与恨,邻居之间的争端与欺凌,主人公的自尊、死要面子、善良懦弱……当然,其中也有平凡人的尊严和渴望,人性的温暖和绵延,在故事的枝枝蔓蔓中闪烁着微光。我们会看到一对亡命鸳鸯,在穷困和绝望中唱着属于两个人的谣曲;看到村里最老、最慈悲的张大孃藏着一段石破天惊的爱情,直到去世……
突破
传统乡土小说范式
如果纯写一个悬疑故事,罗伟章可能比不上那些侦探小说家。纯悬疑故事,一路上升级打怪,一招套一招,走下去。但罗伟章写的悬疑,只是一张表皮,皮下裸露一路粘连着血肉——普通人辛酸样貌、脆弱的人心风暴,以及浸满辛酸与尴尬的人情世故。
小说单行本出版前,在纯文学杂志刊出时就备受文学界好评,在李敬泽、吴义勤、梁鸿鹰、毕飞宇、苏童等国内批评家、作家共同推选下,该小说获得首届凤凰文学奖评委会奖。颁奖词认为这部小说“不仅超越了许多同类题材小说创作的主题呈现,而且也在描写技法上超越了自身的艺术局限,尤其是对人物心理世界的刻画,成为突破传统乡土小说艺术范式的有意味的形式——以一种更加恢宏的时空概念打开了人的内心世界‘隐秘史’。”
对话
罗伟章:时代呼唤有治愈功能的作品
封面新闻:从《声音史》《寂静史》,再到《隐秘史》,为什么对“史”这个字当书名,这么情有独钟?
罗伟章:在写作《声音史》的过程中,有天我想,这个小说写了,我应该再写一部《寂静史》。事实上,《寂静史》的写作比《隐秘史》还更晚些,只是《隐秘史》的单行本出得晚,成了“三史”的最后一部。《隐秘史》在写作之初叫不叫这名字,有些模糊了。当《声音史》《寂静史》发表过后,将那部小说命名为《隐秘史》,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发现,由《声音史》引发的三部小说的命名,都非常贴切,我自己也喜欢。
封面新闻:作为纯文学小说,《隐秘史》的故事冲突非常强,甚至涉及凶杀案。契机或者起意是怎样的?
罗伟章:你说有故事冲突,这就太好了。这是一个心理小说,是主人公和他的另一个自己博弈的小说,我还担心读者读起来有隔膜。事实上不会,很好看。凶杀案是一个契机,然后不断深化。契机是有次我回老家,听我哥说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尸骨,但未能破案,不知死者是谁,是自杀还是他杀,乡里人最终也不知晓。这让我为那具尸骨非常揪心,揪心于他死得“不明白”。我想让这件事明白起来,让他回到皮肉、回到体温、回到种子,便写了这个小说。
封面新闻:作为一个作家,日常思考、为人忧虑,肯定会以某种方式渗透到你的小说写作里。就你而言,一般是以怎样的方式渗透进去?
罗伟章:是的,当然的。这些东西,会体现在某个人物身上。《声音史》里的杨浪,《寂静史》里的林安平和“我”,《隐秘史》里的桂平昌,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承担起写作者自己的部分生命。
封面新闻:抛开完全不读文学作品的人不谈,就算是看文学作品的人,看长篇小说所需要的门槛也高了很多。一方面读者本人要有足够的耐心,另外一方面作品要足够吸引人,要有足够高明的见识和写作技艺。看长篇小说,一个是看语言风格,另外一个是看故事里体现的生命况味、对生存种种困境的思考。从小说作者和读者的角度,谈谈你是怎样的感受?
罗伟章:你说得很对。这也是作家们追求的。去年我去北京领《谁在敲门》的一个奖,同为获奖作家的刘震云说,作家写出一个新小说,不是刚发表刚出版就叫新小说,要对生活有新的理解、新的见地才是新小说。讲的也是作家的理想和努力方向。
封面新闻:《隐秘史》的责编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用了这样的句子:“通过对普通人无法言说的软弱、苦恼、恐惧乃至罪孽进行聚焦显影,用诚恳、坚实而平等的对话,分担精神的痛苦,从而修复人们无法自知的平庸、匮乏与残缺。”你自己觉得这是你想要表达的吗?
罗伟章:确实是我想做的。至于做到了多少,让读者去评判最妥当。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但我说了不算。
封面新闻:这两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少人有一种很深的断裂感。生活有一种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对文学作品治愈力的需求提高了。一个优秀的作家,不大可能对此无动于衷。你是怎样的感受?
罗伟章:是这样的。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当不确定性成为现实的时候,人们便越发死死抓住这种不确定,认为这毕竟是眼前物。也就是说,人们对世界的信心在降低,不大相信眼前物之外的任何事物。这样一来,寻求治愈的动力也跟着降低。这就是很多人更喜欢读非虚构作品的原因。但越是这样的时候,可能时代越是呼唤那些有治愈功能的作品。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作品,呼唤声起,那样的作品就会出现,这是可以肯定的。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