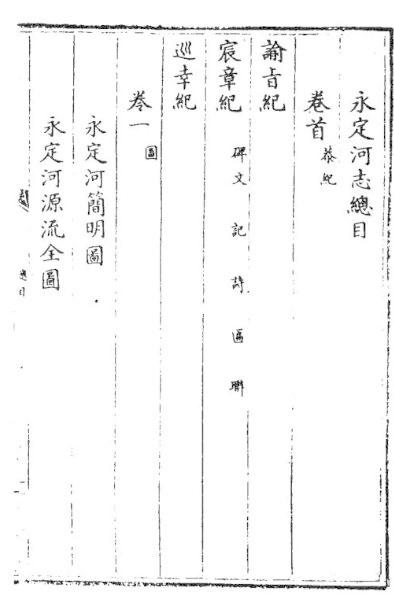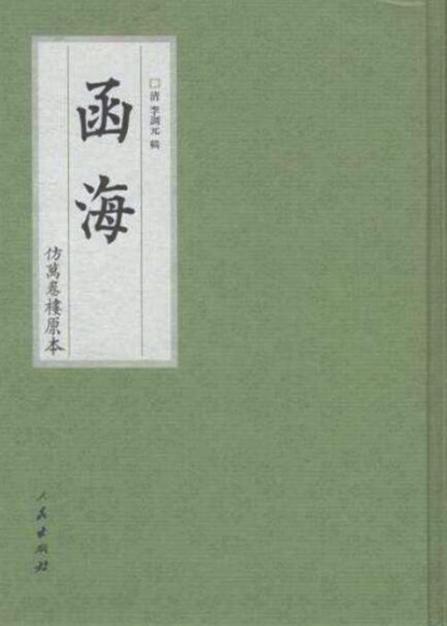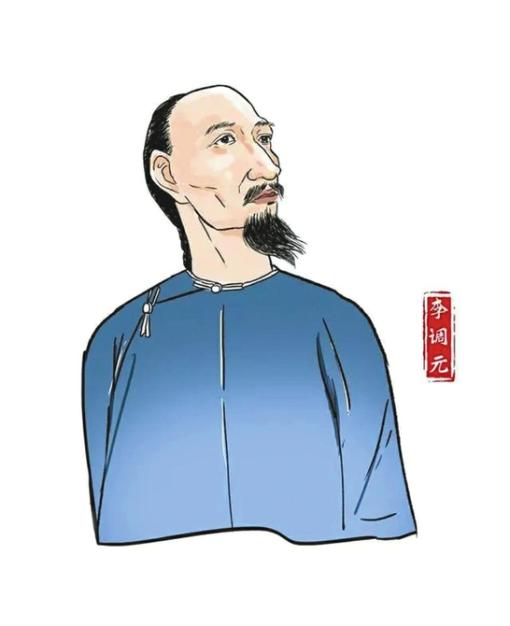李调元与陈琮的旷世之谊
陈琮著《永定河志》
李调元著《函海》
□贾登荣 对于李调元,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李调元是四川罗江人,字夔堂,号雨时,别署童山蠢翁。他生于公元1734年,卒于1803年,享年69岁。李调元一生著作丰富,是与张船山、彭端淑并称为“清代四川三才子”的著名戏曲家、诗人。而陈琮,估计了解的人不多。陈琮是四川南部县人,字国华,号蕴山。他生于公元1731年,卒于1789年,享年58岁,虽然他的名气不及李调元那么响亮,然而,翻开典籍不难发现,他是清代著名的治水专家,其总结一生治水经验所撰写的《永定河志》一书,至今还是治水的重要参考,在业界广为流传。
在清同治年间编修的《南部县志·艺文志》里,收录了李调元的两首诗。一首是《闻永清县丞陈蕴山署永清令》,一首是《哭陈蕴山一百韵》,同时,还收录了李调元写的《中宪大夫永定河道蕴山陈公墓志铭》。从这两首诗及墓志铭中可以看出,李调元与陈琮之间,有着不同凡响的深厚友情。一个是风趣幽默、才华横溢的川西人,一个是不擅交际、忠厚善良的川北人,他们是如何相识、相交,进而结下绵延不绝友情的呢?
同窗锦江边
重逢典礼上
明末清初,经历战乱的四川人口锐减,连省会成都也人烟罕见,变成了虎豹豺狼出没之地。清军攻占成都以后,看到这里一片凋弊,便从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起,把四川省会临时设置在川北的阆中,直到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才迁回成都。为了振兴四川,培养更多治理国家的官吏,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决定,在已经废弃的文翁石室原址上兴建一所公办书院,取名为锦江书院,从全省挑选秀才以上生员到书院深造。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21岁的陈琮怀揣济世之梦,从偏僻的南部县玉镇乡跋涉数日来到省城,入读锦江书院。三年之后,21岁的李调元在跟随于江浙一带任职的父亲李化楠游历多年后回到故里,也进入锦江书院就读。他们两人就在这里相识了。李调元在《哭陈蕴山一百韵》回忆说:“忆昔己卯岁,石室偕文擅。见君于锦江,意气何胜骞。”
在李调元进入锦江书院不久的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25岁的陈琮在乡试中列为“备取副榜”,被送往京师国子监读书,两人就此分别。在国子监学习三年后,陈琮参加吏部选员考试,第二年,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30岁的他被授予顺天府直隶州州判,正式迈入官场。就在这一年,27岁的李调元在科举考试中,高中第二甲第十一名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人生就那么奇怪。分别多年的两个人在一场就职典礼上意外相见了。李调元在“童山日记”中记录了这次重逢的经过:“是日,即到任,先释奠,司礼诸生即陈蕴山(琮)。南部人,由副榜就职州判,赴监业,派往广业堂。向在锦江书院同学,年长,以兄事之。虽不同堂,不敢屈弟子列也。”从中可以看出,陈琮与李调元的重逢,是因为陈琮担任李调元的就职仪式司礼。也就是从这以后,他们的友情与日俱增。
陈琮在京师担任短期官员之后,被派到河北永清县担任县丞(副县令),专门负责河道治理工作。他事必躬亲,极其辛苦,李调元闻讯后,专门从京城寄信慰问,并附诗一首《寄永清丞陈蕴山》:“地尔京畿密,年来报频繁。谁言为政乐,翻似在家贫。树接泸沟远,梁登海淀新。治河闻贾让,不必让前人。”陈琮35岁那年,即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由于其治水有功,被晋升为县令,由从七品变为了正七品,李调元知道这一消息后,马上赋诗一首《闻永清丞陈蕴山琮署永清令》以表祝贺。在这首诗中,他不但对陈琮恪尽职守的踏实作风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对陈琮“暂住为盘桓,赠我紫袍赀”的义举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并说“人生无良朋,何处吐心肝”。也就是说,李调元已经把陈琮视为了知己。
出资赎《函海》
儿女联姻亲
才华横溢的李调元无论是在京城、还是辗转于广东等地为官,始终不忘记做学问。他曾编纂了一部历代四川学人著述的专辑,取名为《函海》。书名出自《汉书·叙传上》“函之如海,养之如春”。这套丛书共搜集图书163种,合编为40函、852卷。一至十函是晋六朝唐宋元明人未刊书;十一至十六函专刻杨慎未刊著作;十七至二十四函兼各种罕见作品,参以考证;二十五至四十函是李调元自己编纂的著作。后世评价说,《函海》堪称一部古代巴蜀文化的“百科全书”。
《函海》编纂完工之后,李调元便将书稿交给一家雕版作坊,请他们进行雕刻印刷。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时,一场大祸降临到李调元身上。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修编印刷成书,乾隆下令将七部手抄本分送全国七大藏书阁收藏。李调元奉旨将其中一部《四库全书》护送到盛京(今辽宁沈阳市)文溯阁保存。在经过永平府卢龙县时,卢龙县知县郭永泰命人把装书的车辆集中停放在馆驿停车场,并盖上茅草防雨。半夜,车辆上盖的茅草忽然着火,看守的士兵赶紧泼水,迅速扑灭了火,保证了书籍没有被烧。不过,在泼水时,有少量水渗入书箱中,让极少数的几十本书留下了水渍印记。当全书送到盛京文溯阁返回京城后,李调元没有隐瞒这一情况,向前来查问的按察使永保作了汇报。而这个永保在吏部任郎中时,就与李调元结下了梁子,于是乘机报复,上奏朝廷,诬告李调元玩忽职守,致《四库全书》受损,乾隆闻讯大怒,下旨将李调元罢官、下狱,并发配新疆伊犁。幸好有直隶总督袁守侗及时相助,以李母年老需赡养为由,百般求情,最终,已经被押送到涿州(今河北涿县)的李调元没有远谪伊犁,暂时在京郊的通州住下来养病。
此时,已经升任正四品永定河道的陈琮,听说李调元蒙冤被关在刑部大牢的消息后,赶紧派人前往狱中探望,并赠送200两银子。当李调元从京城押往涿州时,陈琮又与李调元的堂弟李鼎元一道,将李调元护送到涿州。就在这时,陈琮听说花费李调元大半生心血编纂的《函海》一书的雕版因尾款未付,作坊老板不肯将刻好的《函海》交给李调元,甚至威胁说要毁掉《函海》雕版。陈琮本身并不富裕,但看到朋友呕心沥血的作品有毁于一旦的危险,他马上出资将这部书稿雕版赎回,从而保证了这部巨著的出版。后来,《函海》付梓印刷时,李调元专门写了《函海后序》附于书后,记载了陈琮资助一事。
李调元赎回《函海》雕版后,利用在通州养病的机会,对书稿进行了订正。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朝廷允许其返回四川老家。临行前,李调元专门从通州来到陈琮衙门所在地河北固安县。陈琮留李调元住了三天,并提出两家结为姻亲。李调元的二儿子李榕聘陈琮二女儿,陈琮的第六子陈观林聘李调元的六女儿。李调元非常满意,欣然写下了“道出固安、永定陈蕴山观察留署三日,各指两女为婚,临别留诗二首”,为这次访友之旅画上圆满的句号。
一别成永诀
诗文诉衷肠
陈琮作为专门主管河道治理的官员,在亲自上河道巡视之余,开始著书,将多年来治理水患的得失加以归纳,撰写出一部《永定河志》。成书之后,他把书呈送给直隶总督刘峨。这年五月,乾隆皇帝外出巡视驻扎在宛平县的汤山,刘峨将这部浸透了陈琮心血的书籍呈报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将《永定河志》交给军机大臣们传阅,并下旨让陈琮马上来觐见。陈琮昼夜兼程赶到汤山,受到乾隆的接见。就在乾隆接见陈琮三天之后,陈琮突发疾病,在治河的第一线去世。乾隆闻讯连称:可惜!可惜!并高度评价说:“陈琮自任永定河道以来,经今五年,浑河安澜无恙,皆琮之力!”
直到两个月后,李调元在成都游玩时,才得知陈琮去世的消息,他当即大哭一场。回到住处,李调元久久难以入眠,遥望北方,提笔写下了《哭陈蕴山一百韵》。诗中深情回忆道:“嗟余寡所谐,四海一蕴山。结交三十年,豁达倾心肝。久要金石固,何期沟壑填。暮云一朝断,悲风千里寒。”在诗中,他历数自己30年来与陈琮的交往过程,同时,他在诗中还对陈琮的人品、官德作了评价:“知君无余财,清白贻子孙。”最后他深情地写道:“嗟余虽材下,敢忘夙昔谆。卒为乡人老,空有虚名传。临风北望哭,哭罢天为昏。”诗句中,传递出了李调元对陈琮深深的怀念之情。
此外,李调元还撰写了一篇《中宪大夫永定河道蕴山陈公墓志铭》,对陈琮的为人处事作了全面回顾。他写道:“公生而右手有骈指,为人沉毅慷慨,多智谋,好读书,尤熟悉诸史。其为文渊深雄伟。”“公素疏财好义。固安近京百里,凡在都门京官以及守铨空乏来告者,无无倾囊以赠,毋有吝色。”同时,在铭文中再一次回忆了陈琮帮他赎回《函海》雕版的事情:“余有所刻《函海》丛书,共二百六十种,已负梓人三百刻资,扣板不发,亦公代为赎回。”
一首《哭陈蕴山一百韵》,一篇《中宪大夫永定河道蕴山陈公墓志铭》,将李调元与陈琮之间的旷世之谊,展示得淋漓尽致。